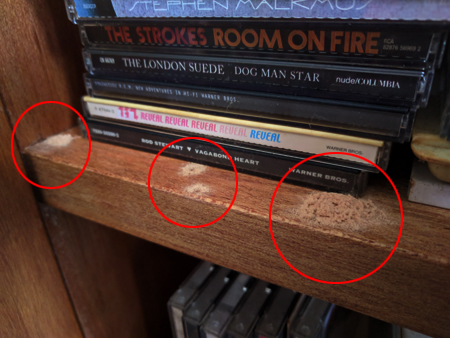我最後一次看到她,是在公司的樓梯間。
那天我上樓,她下樓,我們在一樓和二樓之間的轉角處遇上。她看到我後腳步亂了,突然退了幾步,一臉厭惡。我繼續上前,她退到牆角,臉轉向牆壁背對著我。
她是在三樓工作的新助理,來上班不足半年,習慣不搭電梯。因為她的身材和樣貌姣好,我們這些在二樓工作的中年男人突然全都改走樓梯了。
正當我要問她什麼事時,才突然想到那面懸掛在左耳的口罩。中年大叔走樓梯上樓,口罩不摘下會難以呼吸。
我猜準是這樣沒錯,冠病疫情已搞到人心慌慌,疫苗沒有讓全人類團結,反而是分裂。此時在這樓梯口間,就有兩種人。
我想向她道歉,但我清楚並非出於懸掛的口罩,而是要讓她對我留下好印象,但慾望不該高於原則。
我加快腳步上樓,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,過後聽說她沒再來上班了。
二樓的中年男人們忘了這個年輕女性,我也沒有告訴任何人樓梯口的事,因為在公司內沒戴好口罩是大罪。四個月後才有人談起她。
“三樓那個屁股翹翹的女生死了。”同事拉下雙層口罩後說。
“不要跟我說她中covid,她不是打了兩針嗎?”我拉下口罩時,他已再戴上那雙層口罩。
“你以為只有中covid才會死?”他再拉下雙層口罩:”她在三個月前被診斷患胰臟癌,未期。”
“你他媽的可以不要這樣嗎!?”正當他要再戴回口罩時,我不知為何失控,伸手去扯下他的口罩,對著他大喊,然後找來一支掃把,走向總經理的辦公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