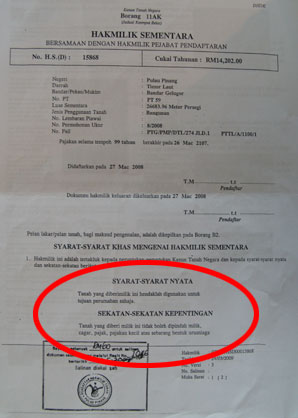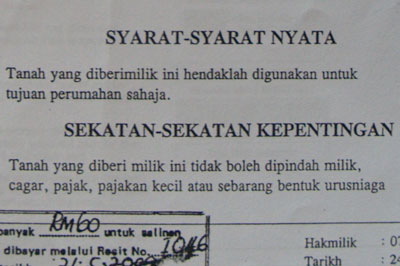今早,很早很早就醒,然後騎摩哆過大橋,去支援我報隊伍採訪補選。到場後我就捲一支煙來抽,感嘆為何電視台的女播報員比平面媒體的女記者都較能看。
答案是:不能看就不用做播報員了。
“kinkyskiny…”
雖然這已是第二次有陌生人直呼我的藝名,但我還是和情婦們一樣,心驚膽跳,擔心一轉臉就被潑鏹水。一轉臉,我就看到一個記者證,上面有一張臉,臉下面是一堆字母:Violet。
原來piew嫂也是同行,但她比較高級,是RTM的producer,她被派來du一個叫做麥仙的女記者。麥仙…這是我這一生人聽過最強的名字了,死都不會忘記。
第一個見面的網友是卡啡(別忘了,還有他的妻子),接下來是與他同blog的姦姐,不久前還有chin。憤青在離開檳城前,我們也見了。最近更莫名奇妙變成了人家的情敵,寫部落格真要命,我最討厭交筆友這種濫情的東西了。
再接下來,就是Violet了。還記得她曾說自己胸小,我偷瞄了一下,她果然誠實。不講這個。我們很奇怪地就談起了piew piew。據piew嫂的說法,piew piew是個手技和口技了得的男人,除了會DIY做水泥,也是吉他老師,而且會吹西洋萧。
我們繼續談著piew piew,但內容不宜爆給你們知道。只是覺得piew piew能找到這種女人,應該非常幸福才對。我希望世上可以多幾個像我和piew piew那樣不想去新加坡上進、賺大錢買大屋駕大車的男人,世界就有得救了。
piew piew,別沉迷五金了,手指要緊呀!不然你就得一世吹蕭。